- 醫(yī)院新聞
- 醫(yī)院動態(tài)
- 綜合信息
- 醫(yī)院院報
- 醫(yī)院文化
- 媒體報道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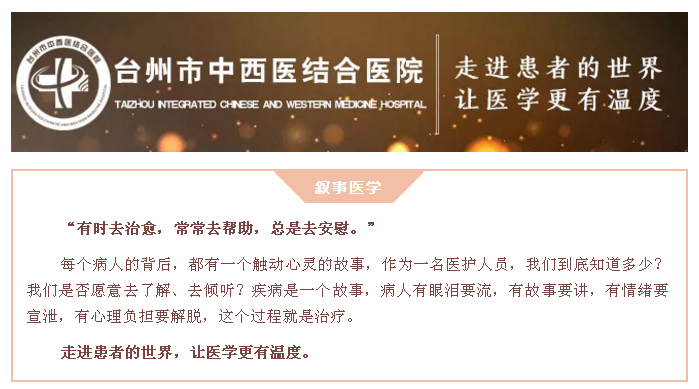

他的世界,我來過
曾有這么一個人,他是夜幕降臨后的掙扎者,是陽光照耀時、眾目睽睽下的逃避者,觸動了我的心弦,我想提著燈去照亮他的黑暗。
那是一個寒風凜冽的冬夜,長長的走廊上看似平靜,偶爾傳來咳嗽聲,北風呼呼的拍窗聲,我們已然習慣與這樣清冷的長夜相伴。
時間流逝好像受到低溫影響一樣,顯得格外緩慢,終于等到巡視病房,獨自守候讓我愈加珍惜漫漫長夜中難得的暖身機會,這是生活給予的暖,讓我們面對平常一樣再平凡再細微的事,都能從中汲取能量,蘊藏著,并傳遞出去。
推門走進病房,漆黑一片,我隨手打開一盞過道燈,突然,“啊”的一聲,只見一個人影從床上猛地跳了起來,一時間動靜很大,換做以前,在沒有戒備之下遭受如此之驚嚇,我怕是早就哭出聲來,但數(shù)年的工作經(jīng)驗提醒著我,凡事都要沉著冷靜。“怎么了!怎么了?”我條件反射性地問著,并立刻打開病房里所有的燈。
只見那人影身上異于常人的皮膚讓我下意識地收回目光,我雙手緊握,猛眨眼睛,盡力祛除掉剛進入腦海的模樣,平復自己加速的心跳。原來那凌亂的異色是一道道大小不一、顏色不同的疤痕,痕跡深淺不同,形狀各異,就像一幅畫被刷子任意地揮灑,縱橫交錯的臉上只有四分之一的皮膚是完整的,傷疤延伸到脖子、手臂,甚至是手指。我沒看清他的身上,也許也是血肉模糊的,看得見的皮膚大部分處于III度燒傷,少許是II度燒傷。
他蜷縮著身體,斷斷續(xù)續(xù)地說著:“我,我以為……是誰……進來了……”看著他,我不禁換位思考,假如我的臉上有上百條刀疤,我會如何去面對世人和陽光?這一刻,我心中了然,微笑著安慰:“不要擔心,不會有陌生人進來了,你安心地睡覺,只是我們醫(yī)護人員會每隔2個小時巡視一次。”
我很想問他之前到底經(jīng)歷了什么,可又忍住咽回去了,去重新揭他心里的傷疤,應(yīng)該會比他現(xiàn)在的痛還痛。他可能接受過許多異樣的眼光,也忍受過別人的歧視,對他來說,平等的對待才是給予他最好的安慰。
“過2個小時,我會再來的,下一次可不用害怕了哦。”我?guī)退仓煤昧梭w位,再拉好床欄就離開了。交接班的時候,我強調(diào)了他的情況,希望同事們能有心理準備,并以平常心對待他。
接下來的幾天,他的床位由我負責,我深知他懼怕別人的目光,所以我決定不再看著他,無論是發(fā)藥、護理還是路過的時候,我都盡量將眼神掃向別處。我以為這樣的方式對他是最好的,可是我發(fā)現(xiàn)他自此總是戴著帽子、低著頭。
“會不會是我的舉動刺傷了他敏感的心靈?”我反思著,都說微笑是治愈心靈最好的方式,于是我決定改變策略,微笑面對,無論何時,無論何地。有次打點滴,我微笑著把目光鎖在他身上,輕輕地拿起他那千溝萬壑的手,心無旁騖地尋找著靜脈。他不由自主地縮了一下手,低著頭說:“我的靜脈不好找……打不進也沒事的……”“我見過許多情況更復雜的,你的算還好。”我一邊勸慰一邊摸索,不放過每一寸皮膚,總算在關(guān)節(jié)處的一處角落上找到了目標,小心翼翼地成功扎了進去。這時,在他殘缺不全的臉上浮現(xiàn)了一絲笑容。我想,比起在黑暗中,他更需要站在陽光下。
后來,他的隔壁床來了位阿婆,一進門就被他嚇了一跳,然后嚷著要換床位,頓時氣氛尷尬,他又低下了頭,用帽沿遮擋著臉。“阿婆,在這里的都是病友,首先要相互理解尊重,而且現(xiàn)在床位緊張,這張是最好的了。”在我的努力勸說下,阿婆終于平復下來,安心入住。隨后,他朝我笑了笑,不再像之前那么吝嗇他的笑容。
又是一輪夜班,來到他病房前,我躊躇不前,怕會驚醒他,但必須要進去巡視,我輕輕地進去了,他居然酣然入夢,還打起了呼嚕,我知道他已經(jīng)解除了對陌生環(huán)境的戒備。我很欣慰,原來每天的努力,真的會換來他人的陽光。再之后,他的妻子來看他,他從容地從妻子手中拿過包,拉著她一起坐在床邊,然后聊起生活中的事兒,談笑風生,其樂融融的。這從天光乍破走到暮雪白頭的模樣,我仿佛看到了生活正對他打開新的大門。
每天穿梭于形形色色的人群中,也許我們只是過客,但是他們的世界,我來過,也參與過。每天給予一點點暖,或許不能使體無完膚的人光彩依舊,但會讓他明白世間還有許多色彩;或許不能使病入膏肓的人立即痊愈,但會讓他知道希望比鉆石更寶貴。我們正是這樣的提燈者,讓沉淪在病痛的人在逆光幽徑中看見光明。
作者介紹

王朦佳
臺州市中西醫(yī)結(jié)合醫(yī)院消化內(nèi)科護師。
The End
